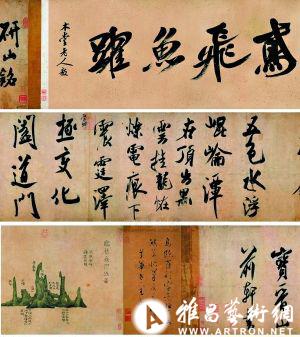
从2009年至今,我国的文物国家优先购买权采取的是一种“拍后先得”模式,即在拍卖成交之后的7天内,国有机构可以“横刀夺爱”。最近,嘉德春拍上包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等11件拍品被文物部门宣布国有机构享有“国家优先购买权”,最后,其总成交价超过最高总估价两倍多。拍卖结束后,“拍后先得”模式再次引发业内人士关注,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人说,这种模式只会成为拍品价格的“助推器”,而有人则认为,这种模式是历史的进步。
正方——
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东溟:
可最大程度保护委托人利益
我认为,国家优先购买权事后行使的“拍后先得”模式是历史的进步,有效保护了委托人的权益,但细节尚待完善。
在“拍后先得”模式出现之前,拍卖文物时经常会遇到非常尴尬的状况。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2003年中国嘉德春拍时1447号拍品——《书蔡氏传纂疏》元泰定四年(1327年)梅溪书院刻本,在拍卖之前已被文物部门定为一级品,按规定只有国有机构才可以竞买,但有私人藏家对此并不了解,也参与了竞拍,并且打败了同场竞拍的国有机构。但最后我们只能遗憾地通知他没有资格买,该拍品也被退掉了。
送拍的东西如果被定级为一二级文物,本来应该是一件挺光荣的事情,但是按照之前采取的“会下沟通”或者“定向拍卖”的方式,反而意味着该文物的成交会受到种种局限,即便成交了,价格也被压得比较低。长此以往,会扼杀委托人的送拍热情。相比之下,目前采用的这种国有机构事后享受优先购买权的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以最大程度上保护委托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然而,目前这种方式在细节上仍有尚待完善之处。首先,关于什么是“国有机构”的定义并不清晰。去年拍卖“过云楼藏书”,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在竞争时就曾提出,北大图书馆不能算是文物收藏机构。但是,一直到最后,国家文物局也没有就这个行使主体的范围给出明确的答复。这是一个漏洞,如果不填补,今后类似的纷争还会有。其次,“拍后先得”模式对竞拍者所承受的损失考虑不周。如果拍后7天内国有机构行使优先购买权,就意味着竞买人是在替国家举牌,空欢喜一场。虽然他并没有物质上的损失,但感情上可能接受不了。在实践中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引起过一些混乱。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可以更加完善一些:比如给予竞买者一定的精神或者物质奖励。我相信,如果将细节做得更完美,目前这种“拍后先得”模式是一个不错的制度。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刘双舟:
国家优先购买权确有必要
文物不仅有经济属性,还具有历史和艺术属性。从财产权上来看,它可以属于某个个人,但它的文物价值应该是国人共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对某些重要文物享受优先购买权是有必要的,因为国家保护更能够完整地体现文物的价值,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规定。
1949年以来,国家对私有文物的取得方式曾经发生过几次变化。最初,私人收藏的文物是不能进入流通领域的,只能向国家捐献,或者由指定单位进行收购。一直到2002年《文物保护法》进行修订时,才在第58条中规定:“文物行政部门在审核拟拍卖的文物时,可以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优先购买其中的珍贵文物。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的代表与文物的委托人协商确定。”
从2002年至今的文物拍卖实践中,国家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模式先后具体表现为“拍前协商”模式、“拍中定向”模式和“拍后先得”模式三种。“拍前协商”模式相当于“私订终身”,文物不经过公开拍卖竞价,价格通常被压得比较低,侵害了委托人的利益,打击了他们出让文物的积极性;之后又做了“拍中定向”模式的尝试,让文物进入拍卖流程,但只有文博机构才有资格进场竞拍。这样做也有问题,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只有一个竞拍人,形不成竞价。目前的“拍后先得”模式是由“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第2833号拍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案例首创的。与之前的两种模式相比,这种模式有了一定的进步,弥补了《文物保护法》58条在操作上的漏洞——对文物而言,可以形成合理的市场价值,同时,也有效保护了委托人的利益。
尽管这是一种进步,但也还是存在着一些尚待改进之处,首先,优先购买权应当在拍卖程序中完成;其次,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主体应该在拍卖前就被明确,而不是在拍卖成交后才露面。如果用真爱作比喻,“以情夺爱”是可以理解的,但“横刀夺爱”就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了。在文物优先购买权的问题上,政府不应做“刀”。我认为,拍卖前明确优先购买权主体的身份,并且在拍卖程序中行使这个权利会让我国的国家优先购买权制度更加趋于合理。但是,目前这样做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文物保护法》的相关条款早已到了该做适当修改的时候了。
反方——
北京天问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 季涛:
“贪便宜”心态有违《合同法》
在文物拍卖过程中,国家优先购买权采取的“拍后先得”模式不公平、不合理,也不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据我了解,文博系统行使优先购买权先后有过几种方式:1995年故宫收购翰海拍卖《张先十咏图》时,文博机构没有公布身份,现场电话委托竞价;2003年故宫收购嘉德拍卖隋贤书《出师颂》,是拍卖前与卖家私下沟通,谈好价格直接收购;第三种方式就是自2009年至今北京行使的拍卖成交之后7天,以落槌价截走。最后这种最不合理、最不公平。
《合同法》有明确的规定,“优先购买权”需要购买方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但事后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文博机构,并未参与拍卖场上的同台竞争。不符合《合同法》“同等条件下”的要求。竞拍者在场上竞价成功,签署了成交证书,拍卖结果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某个文博机构可以凭文物局下发的一个红头文件,就跳出来跟人家抢东西,这很不地道,从法理上也讲不过去。
事实上,同等条件下行使的优先购买权,在非艺术品领域的实践已经非常成熟。具体操作方式就是,优先权人可不参加前面的竞价,但在拍卖师报“三次落锤提示”的“最后一次”时,要转向优先权人。比如,拍卖师说:“现在场上的出价为38万元,38万元您有兴趣吗?”如优先权人说“不”,则拍卖师落槌,宣布前面非优先权竞买人成交;如优先权人说“我要”,则拍卖师转向大家:“优先购买权人出价38万元,还有加价的没有?下面的价位是39万元!”如果没人再加价,则拍卖师落槌宣布优先购买权人成交;如有人继续加价,则拍卖师继续向全场报价,直到“最后一次”时再转向优先权人,依此继续类推。这种方式完全可以被应用在文物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中。
事实上,之所以文博机构不进场参加拍卖,非要“拍后先得”,并不是技术上有何障碍,讲得直白点儿就是为了贪图便宜。文博机构如果进场拍,拍品的价格很有可能被助推得更高。目前,有关部门虽然已经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应当尊重委托人的利益,但还是有一些贪便宜的心态在作祟。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陈少峰:
与其优先购买不如完善登记制度
在我看来,与其强调国家优先购买权,不如建立完善的文物登记制度和展示制度,以充分发挥文物的价值。
我注意到一些被行使了优先购买权的文物,实际上并无必要被国有机构购买。比如说北大图书馆去年要买的“过云楼藏书”,这套古籍的价格可以说跟我们学校的财力是完全不相符的。而且,它的学术价值非常小众,我实在看不懂一个综合类大学的图书馆有何必要花费重金去对这样的文物行使“优先购买权”。
私人手中的文物非常多,国有机构以其目前的财力,根本不可能买得完。我倒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文物,太多地使用国家的钱去干预并不好,与其将精力放在力促国家机构优先购买,不如建立比较完善的登记制度。国家有关部门只要对文物在谁手里,对其保管状态了然于心即可。即便私人没有妥善保管的能力,也可以靠寄放在文博机构的方式来解决。
归根结底,文物在个人还是国家手里其实并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交易和展示的机会,充分发挥其经济、学术、文化上的价值。对于这些事情,国有机构收藏并非就一定比私人收藏更有优势。有很多文物到了国有机构就被束之高阁了,这和私人藏家从此就将文物锁在私人保险柜中不愿将其示人同样糟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文物允许借阅和展示做一些规定,或许比力促国有机构来收藏来得有效。而对于那些有明确的、成体系的收藏目标,不仅有能力妥善保管文物,还愿意拿出来做专题展出的私人藏家,我们应当鼓励,而不是认为私人收藏天然地比国有机构收藏差了一等。
总之,文物在谁手里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让文物能够被妥善保管,其价值能够得到体现。